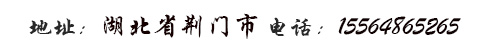陈连春木瓜
|
前些年,学校到杨梅路口市场,路旁长着一棵木瓜树。往日,出入间,我多是骑着电动车驰过,没多留意它。 有日,步行途经,竟发现,树上结着许多木瓜,堆叠着,大小相杂其上。每一瓜梗处夹杂着数花,色白透着淡黄,鲜嫩,靓丽。叶梗长长的向外伸出,把叶撑开,叶间约有六七主叶脉,每一叶脉两边的外形,呈锥形状起伏。如一个心手巧妙的女子,用剪刀把筐大的绿叶剪成图案,挂在树梢上,向意中人展示自己的心思似的。但这图案并不是机械般的图案,它随意多了,变化多了,也因此自然多了。由于介于有序与无序间,更有美感与生意。这一令人心赏的木瓜树,只因放慢脚步,才发见它的美姿,得以深赏。 那时,学校没实行封闭式管理,门口路边附近,有许多摊车,摆着小吃或水果在卖。每放学时,热闹非凡。有时,妻下班回来,见着有木瓜卖,不时会买一二个。饭后,捎掉木瓜皮,切成几大块,剔除瓜心带籽的地方,放于白瓷碟上,一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。弥满口齿间的香甜,倾刻间,足以消尽终日的劳累,又何尝不是一种日常间的幸福呢! 妻与孩子都喜欢吃,不知为何,我却不喜欢。所以,一直来,我从未吃过木瓜。至于它的味道如何,我无从知晓。 木瓜的形状、色相,外质内妍,入画甚亦可观。记得大学升考前,有一次,上色彩课时,画室的老师把好端端的一个木瓜切开,一半敞开肚子放着,瓜籽黑亮黑亮的,瓜肉的颜色有过渡,从黄到橘红,很自然,亦很好看。另一半正身,深绿色,与敞开的一半交搭放着。因极少画,结果画室很多人画得一塌糊涂,我便是其中的一个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! 八大的画册,曾有一幅木瓜图,寥寥数笔勾括叶与瓜的形体,再淡淡色彩点染,数百年间,依然活色生香。八大画的木瓜图,尤其是画中的叶子,与我现实中所见的木瓜叶如此迥异,这给我造成不小的疑惑。后百度上查找资料,据《岭南杂记》记载:“我国于十七世纪,从国外引进番木瓜种植,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。”另一种说法,宋代王谠《唐语林》说:番木瓜传入中国,至迟应在十二世纪,最早可能推至唐代。 原来,我平日所见、所说的木瓜,其学名是番木瓜,原产自南美的。而八大画的才是正宗的本土木瓜。现实生活中,由于大家说习惯了,却把木瓜前“番"字省略掉了,结果,容易与本土木瓜混指同一物。 正正宗宗的本土木瓜。早在几千年前,《诗经》曾有诗句云: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”这样隽永的文字,象征着美好的爱情。彼时,爱情较为纯洁,送草、送瓜都情意绵绵。当今,爱情更多是物欲与虚荣心在撑满,早已不再有童话般的故事了。 在南方,木瓜树很常见的。长安画派的石鲁,曾有一代表画作《家家都在花丛中》。那是年,石鲁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邀请,来广东新会参加全国部分省市美协的工作会议。当石鲁从苍凉荒芜的西北,来到了花团锦簇的南国时,不同地域的风物景象,使他内心欣悦激动起来。随即,他打开自带的画具纸笔,对着木瓜树、芭蕉、棕榈、榕树和开满了红花的凤凰树写生起来。这些前所未见过的南国风物,在他笔下表现得十分美好且诗意浓郁。那棵木瓜树,独独安排在画面最前,可见,木瓜树的靓丽姿影,让石鲁应是难以忘怀的。 文革时,石鲁曾一度被迫疯,流落街头。我曾在一书册上,见一图片,是他晚年住院时所拍摄。他那久未理过的头发,如冬日里的枯草蓬散凌乱。谁会想得到?一个深爱生活的大画家,却遭如此时际厄运。想及,真让人怅然! 木瓜外形的形色,未熟透时,与冬瓜有些相似,但形体较冬瓜小许多,故有小冬瓜之称,因长在木树上,乡里人俗称柴冬瓜。何以“柴"字称谓,乡俚谓“柴"与“木"字,也许会有某些许相关延伸所指,用普通话的语境思维去考虑看待,是很难理解明白的,这也是方言独特的地方。现在,小孩从幼儿园开始,就推行普通话化了,方言的语境越来越小了,越来越淡了。 有日回乡,在书舍与友人闲坐时,聊及木瓜时,友人说:“身体有内伤的人,不宜吃木瓜。"友人是个习过武的,一身功夫,就独独怕木瓜。 (图片提供:陈连春) 作者简介 陈连春,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员。 滨海作协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muguaa.com/mgrybw/1106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这8款蔬菜下奶效果赛猪蹄,奶多人瘦做辣妈
- 下一篇文章: 静心和歌唱可以治愈世界喜悦心身心疗愈冥想